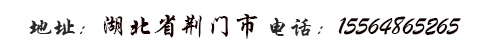茸听古色之美物色之黑黑釉瓷
|
《古色之美》 作者:青简 两千多年的陶瓷史中,黑釉瓷就如同它的颜色一样,低调而沉默着,可它确实存在,是能被抚摸把玩却深深无语的存在。如果说利用渗炭技术烧造的黑陶,是追求“黑如漆,声如磬,薄如纸,亮如镜,硬如瓷”的刻意行为,那么早期东汉瓷器中的黑釉,就只是因为土质含铁量高,而呈现的无可奈何。 黑釉鸡首壶(东晋) 至两晋时期,黑釉从懵懂的不期而至,到模仿漆器的有意为之,完成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审美转变。在魏晋玄学的背景下,德清窑烧制的大量精美黑釉器物,如黑釉盘口壶、黑釉鸡首壶等,为士人们隐逸恬淡的生活,奉上了最简约朴素的色彩。 唐代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中,也能找到黑釉幽微的影子。唐代有一种特别的瓷器,叫作缁素瓷。它多为茶器,和同时期的其他器物截然不同,其有外黑内白的鲜明特征,在浮翠流丹的唐代有些许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意味。僧人着缁衣,缁便代指僧人;俗家人多穿白衣,素就与缁相对,代指俗人。所以缁和素既指黑白两种颜色,也暗合僧俗两家因为茶而走到一起。“茶,香叶,嫩芽。慕诗客,爱僧家……”佛缁、俗素在一杯清茶里看似融合,却又泾渭分明。而此类瓷茶具、外璧黑得深邃,循乎缁门仪轨;内里白得纯净,宜于品观茶汤,颇受大德高僧及文人雅士钟爱。史载,诗人王维,常云游于长安各大寺院和终南山间,于吟诗泼墨之暇,嗜茶如命,其携行出游之茶铛,能够与考古发现互证互鉴者,恰为外黑内白之瓷。 建窑兔毫盏(南宋) 与茶有着不解之缘的黑釉,到了宋代独放光芒。宋代饮茶以“点茶”为主要形式,即先将饼茶碾碎,置碗中待用。以釜烧水,微沸初漾时即冲点入碗,再以茶筅用力打击,泡沫就会慢慢出现。而泡沫出现的速度、颜色、纹理与持久性则成为“斗茶”的标准。“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,青白为次,灰白次之,黄白又次之”,一句话概括就是泡沫白者胜出,而黑是最能衬托白的底色。难怪宋徽宗在《大观茶论》中写“盏色贵青黑”。建盏应运而生,同时期定窑、耀州窑、吉州窑、磁州窑、山西怀仁窑等,也都纷纷烧制各种黑釉瓷器。然而大儒蔡襄评价“建安所造者,绀黑,纹如兔毫,其坯微厚,熁之久热难冷,最为要用”,其实除兔毫之外,建窑烧制的黑釉瓷,黑中有变,变化万千,包括兔毫、油滴釉(鹧鸪斑)、曜变釉、结晶冰花纹釉、芝麻花釉、龟裂纹釉等。凝视这些不同纹理的结晶釉,仿佛深邃的夜空,斗转星移,变幻无穷,黑再也不是所有颜色的尽头,而是一种新生。 乌金釉双象耳瓶(清代) 当铁蹄踏入中原,也打碎了现世安稳的一枕黑甜。浓郁的色彩席卷了陶器界,黑悄然退居于角落。经历了金元时期的低谷,黑釉在明代永乐年间昙花一现,直到清康熙年间,景德镇瓷工利用含铁量达13.4%的乌金土烧制出一种光润透亮、色黑如漆的纯正黑釉。同一般黑釉相比,除了含铁量高以外,乌金釉还含有锰、钴等元素。它是黑釉中最莹亮的一种,让黑而不知其为黑,只记得它的光华灿烂与绝世风骨。 黑釉一直徘徊在历史的幕前幕后,古人曾试图摆脱它,它却最终化被动为主动,在敛尽风华后,创造出一种黑色的光芒,于无声处有惊雷。 ——END—— 精彩回顾 茸听┃《新卢浮宫之战》之瓦洛瓦街茸听┃《今日宜逛园》三山五园的万千景象之八景传承茸听┃《这幅画原来要看这里》十字架欢迎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luronga.com/lrsz/744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大荔县教育局名师提升工程系列之ldq
- 下一篇文章: 一个可以救命的茶包ldquo台湾红藜